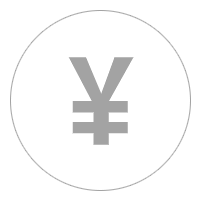颐和园管理处研究室副主任张鹏飞。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颐和园管理处研究室副主任张鹏飞。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北京文化守护人张鹏飞,颐和园管理处研究室副主任。2014年从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硕士毕业后投身颐和园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十年如一日地深耕于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幕后”,让古籍中的颐和园“重新说话”。他从浩如烟海的图档和文献中抽丝剥茧,从解读颐和园“样式雷”图档的古建“密码”,再到用御制诗文破解颐和园中的哲学意境,他的研究不仅为古建修缮保护提供了关键历史依据,更将颐和园遗产价值阐释维度不断扩展。

作为北京旅游的顶流打卡点,颐和园的新建宫门每天游客熙熙攘攘。身侧是碧波荡漾的昆明湖,远眺是林木蓊郁的万寿山,徜徉在湖光山色间,令游客流连忘返。
园墙之外一路之隔,颐和园管理处则清静了许多,在被书架塞满的办公室里,颐和园研究室副主任张鹏飞从两摞高高的书稿中探出头来。在他的电脑屏幕上,一张张电子版的古建“设计图”被放大和细细观察。这些来自一百多年前的“样式雷”图纸,隐藏着古人对古建筑的设计理念、美学和哲学思想,张鹏飞则要解读出这些设计“密码”,这对于古建未来的保护修缮至关重要。
颐和园是我国现存最完好、规模最宏大的古典园林,199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了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张鹏飞每日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大海捞针一般地汇总颐和园相关信息并加以研究。“遗产保护强调研究先行,我们要弄清楚颐和园古建和景观在每个时代的历史特色,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保护遗产。”
养云轩内曾经打开的四扇窗
暑期,长廊无疑是颐和园人流量最大的景区之一,游客驻足抬头,欣赏精美的彩画,走走停停之间,这条我国古典园林中最长的画廊出现“拥堵”。一些躲清静的游客向北一转,眼前又出现了一座精美的建筑组群——去年10月刚刚开放的养云轩。
“天外是银河,烟波宛转;云中开翠幄,香雨霏微。”这是乾隆皇帝题在养云轩钟式门上的对联,点出了养云轩的烟云姿态。“养云轩前有昆明湖,背靠万寿山,水汽在此汇聚蒸腾。养云就是希望下雨,这座建筑体现了皇帝对农业的重视。”张鹏飞不善言辞,但对于颐和园古建的典故,他总能娓娓道来。
养云轩意为“养蓄云气之轩”,曾经是格格、侍从的休息之所,如今成为清幽的学术交流场所,大量颐和园文化研究成果书籍在正殿中陈列。在此次对公众开放之前,它曾经作为颐和园的办公场所使用多年。当年在这座院落办公时,工作人员不曾注意到,配殿南山墙上,有几道窗户被封堵的痕迹——堵窗的砖头略微外凸、砖头之间的缝隙也有点大。但前不久在样式雷图档研究中,细心的张鹏飞发现了端倪。
他摊开了一张“养云轩地盘全样”样式雷图。图上清晰可见一个葫芦形状的莲塘,上架一座拱桥,莲塘北面,是正殿、配殿等建筑。“有三张图的配殿南墙上,绘有四扇窗,另外两张则没有窗。”
 颐和园养云轩地盘全样。图/《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颐和园卷》
颐和园养云轩地盘全样。图/《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颐和园卷》窗子的消失涉及一段尘封的历史。颐和园的前身是清漪园,于1750年(乾隆十五年)开始建设。1860年,随着英法联军的入侵,清漪园被烧毁。1886年起,清漪园开始修复,1888年改名为颐和园,到1895年历时九年修建完成。虽然当时国力衰微,但颐和园仍然保留了清漪园的主体风貌。在1860年英法联军的劫火中,养云轩幸免于难。1888年,颐和园重修工程公开后,养云轩也列入维修计划。
张鹏飞拿着样式雷图,再次来到熟悉的养云轩实地勘探。“这四扇窗的痕迹目前仍存在养云轩两配殿的南山墙上,可以作为养云轩没有被毁的证据之一。”通过查阅《颐和园内外拟修各工清单》《清宫颐和园档案•营造制作卷》等大量资料并仔细研究样式雷图,张鹏飞将养云轩的历史变迁整理还原出来——
给乾隆母亲崇庆皇太后庆祝六十岁寿辰所做的《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是养云轩最早的图像资料,画中可见两配殿南山墙开有四扇窗户。打开窗户,通过长廊眺望美丽的昆明湖湖景。光绪年间,颐和园重修时,养云轩虽然没有被焚毁,但是正殿增加左右顺山房各三间,配殿南增加左右值房各三间。
 养云轩东配殿南山墙四扇窗痕迹。受访者供图
养云轩东配殿南山墙四扇窗痕迹。受访者供图“在为修缮而绘制的样式雷图上,原来的建筑用黑线条描绘,而这些新增的房子,用红笔勾勒出来。”他解释说,由于配殿南侧增加了值房,南山墙的窗户即便打开也不见风景,失去了作用,后两张设计图中便将窗户舍去,实际施工中也对窗户进行了封堵。
通过研究,张鹏飞发现,乾隆眼中养云轩的建筑布局是舒朗的,但光绪年间,顺山房和值房等的增加使院内建筑更加紧密,失掉了原有的山林氛围。“这种变化主要是功能上的差异所致,乾隆时期,养云轩是作为休闲休憩的场所,而光绪时期则变为了居住场所。”
养云轩中紧邻的配殿和值房,过道容不下两人并排行走,几乎没有游客途经此地,墙上是否曾经开过四扇窗,也很难察觉。为何还要下大力气研究它?
“在这方面,还必须得较真儿。”张鹏飞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原真性需要得到保护。将来古建修缮时,工人不能直接把窗户曾经的痕迹抹去。“如今后人做的每一步,都要有历史依据。要通过我们的研究,找到这些历史依据进行佐证。”
破解“样式雷”图档隐含的秘密
2014年从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专业读完硕士后,张鹏飞来到颐和园研究室工作。在研究室原主任赵晓燕的印象中,张鹏飞做事踏实、爱看书,“本来脑子里东西就多,记性还特别好,归纳总结能力很强。”
对于曾经的下属,她不吝赞美之词——无论颐和园办讲座需要制作PPT还是办展览需要材料,张鹏飞总能凝练出最简洁精准的文字。得益于勤勤恳恳的实地走访和大量阅读,他俨然成了颐和园的“活档案”,这为他把浩瀚的文献融会贯通,从而进行颐和园专项研究打下了扎实基础。
最初的几年,张鹏飞的研究大多基于文献记载。他坦言,这些工作其实相当枯燥,他要从大量已知的知识中寻找“未知”,再将它们整合起来,寻找关联开展研究。随着《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颐和园卷》于2018年出版,他的研究多了更为翔实、直观的辅助工具。
“样式雷”是建筑设计世家,负责宫殿、园林、坛庙、陵寝、府第、城垣、河道、内檐装修、露天陈设等工程和器物的设计。雷家几代人先后参与和主持设计建造了故宫、天坛、圆明园、颐和园等著名建筑。“样式雷”图档包括雷氏家族制作的建筑图样、烫样、工程做法及相关文献,目前大多数收藏于国家图书馆。
“最初,我们大量翻阅藏书,收集到的‘样式雷’图档只有27张,不成体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颐和园的‘样式雷’图档后,可供我们研究的图档达到1000余张,基本涵盖了颐和园的所有景点。”张鹏飞如获至宝,研究室于2020年启动了《颐和园样式雷图档编目与研究》。通过研读这些珍贵的古建工程图纸,他们得以了解颐和园的古建布局、功能变迁和景观环境,更加细致地感受古代工匠的设计理念,从而加深对颐和园的认识。
 张鹏飞在办公室查阅资料。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张鹏飞在办公室查阅资料。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样式雷”图档种类繁多,有最直接反映建筑布局的地盘样、可以直观感受建筑形态之美的立样、处于设计初始阶段的底样……图样和档案中更是有着大量的古建专业术语,如何弄明白这些术语的含义?张鹏飞直言,这是个自然而然、熟能生巧的过程。轻描淡写背后,是他反复请教专家、查阅资料,大量看图并到现场进行比对的积累。
就这样,一张张图被他“翻译”“解读”成论文,颐和园的历史变迁被清晰还原。“由于1860年大火,导致我们对颐和园前身——清漪园认识不足,在文献缺少的情况下,‘样式雷’图档的意义就非同寻常。”在对比并研究《清漪园地盘画样全图》《南湖畅观堂地盘样》等‘样式雷’图档和《清漪园山前山后南湖功德寺等处破坏不全陈设清册》《畅观堂等处陈设清册》等大量文献时,他敏锐地注意到畅观堂的变迁,并还原了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和乾隆时期清漪园的畅观堂相比,慈禧时期颐和园的畅观堂在建筑布局、建筑样式上都发生了改变,比如庭院中围合的小湖被填平,一些原有的亭子也被拆除。”
张鹏飞说,研究“样式雷”图档可以了解建筑的建造过程以及工程做法,对于未来的文物保护和修缮有具体的指导意义。“把它们解读清楚,对于园林绿化部门景观营造、植物保护也有借鉴意义。比如在有的图中,我们发现古人进行改扩建时,会避开树木,如今,这些树木已经长成古树。”
在研究过程中,张鹏飞也对“样式雷”图档的识别提出新的见解。“可能由于年代久远,建筑名称标识脱落,也可能是对于图中描绘事物不够熟悉,在已经出版的‘样式雷’图档中,整理者将一张畅观堂‘样式雷’图错认成文昌阁东南面院落地盘图样。”早已将颐和园建筑分布记在脑海中的张鹏飞,则认为应该是畅观堂,并通过同一位置的图样对比得到印证。
在张鹏飞的带领下,研究室成员已根据样式雷图档撰写了多篇文章,被细致研究的古建包括园中的无尽意轩、清华轩、介寿堂等。
通读乾隆御制诗文4万首
今年,张鹏飞又带领研究室开启了一项新工作——整理出版清漪园御制诗文集。御制诗特指帝王亲自创作的诗歌作品,它们是现代人了解清漪园的重要途径。
“乾隆皇帝很喜欢清漪园,他有1000多首御制诗都跟清漪园相关。不过他同样爱作诗,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从4万多首诗当中提取跟清漪园有关的1000多首,本身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张鹏飞坦言,为此,他们通读了十大厚本《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集》,大海捞针般地遴选出了带有清漪园景点的诗文。
他们很快又遇到了另一个难题。乾隆造园有一个特点,即一个名称的建筑,在好多园林中都有应用。比如避暑山庄和清漪园都有夕佳楼,清漪园和圆明园都有山色湖光共一楼。为了弄清楚诗文中提到的建筑确属清漪园,还需要进行多方对比。“比如乾隆十八年的《宿云檐》这首诗,前后都是描写避暑山庄的诗作,通过前后关系,我们断定这首诗写的是避暑山庄的宿云檐,而非清漪园,所以在我们新出版的诗文集中将不予收录。”
在整理过程中,研究员们还发现了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些字少了几笔。张鹏飞带领大家探讨,并逐步意识到,御制诗中采用了缺笔避讳的形式,比如乾隆皇帝的名讳弘曆,诗中写到弘时,就会少写最后的一“点”。道光皇帝的名讳旻寧,寜字便会少写最后的两笔。“一些皇帝的名讳是不太常见的,比如嘉庆皇帝的名讳顒琰,所以我们也是摸索了好久才发现了这个规律。最终,我们确定将这些缺笔少划的字予以保留,将真实的历史信息传递下去。”
 张鹏飞在查阅文献。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张鹏飞在查阅文献。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谈及收集和研究御制诗文的意义,张鹏飞以知春亭为例,亭子在文昌阁西边小岛上,其含义此前一般认为是源于诗句“春江水暖鸭先知”,但通过阅读御制诗,他发现“春”并非实指,而是具有象征意义。
乾隆在《知春亭有会》一诗中写道:“春为乾之元,气居四时首。万物无不知,而亭胡享帚。亭固物之一,一实万之母。仁仁与智智,其见随所取。一知即万知,义具系辞有。”张鹏飞解释说,在乾隆看来,春就是《周易》乾卦四德“元亨利贞”中的“元”,代表万物之始,乾元以统天。“这首诗也说明知春与《周易》的深厚渊源。所谓知春就是知万物及其运行规则,并以仁德之心顺应之。”他认为,乾隆皇帝将位置绝佳的亭子命名为知春,昭示着他临民体仁之意,意在施仁政以滋养万民。
正是源于张鹏飞和同事们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颐和园这座世界文化遗产鲜少为人知的细节正在逐步为公众所知晓,颐和园遗产价值阐释的维度也在不断地扩展。
新京报记者 张璐
编辑 张磊 校对 杨许丽

猜你喜欢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